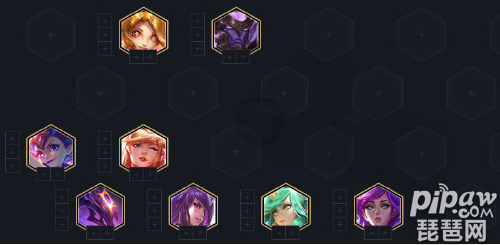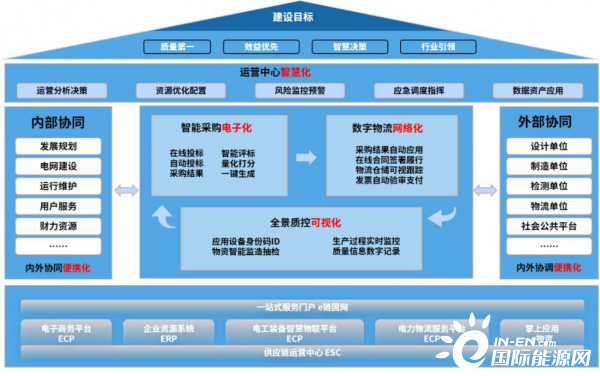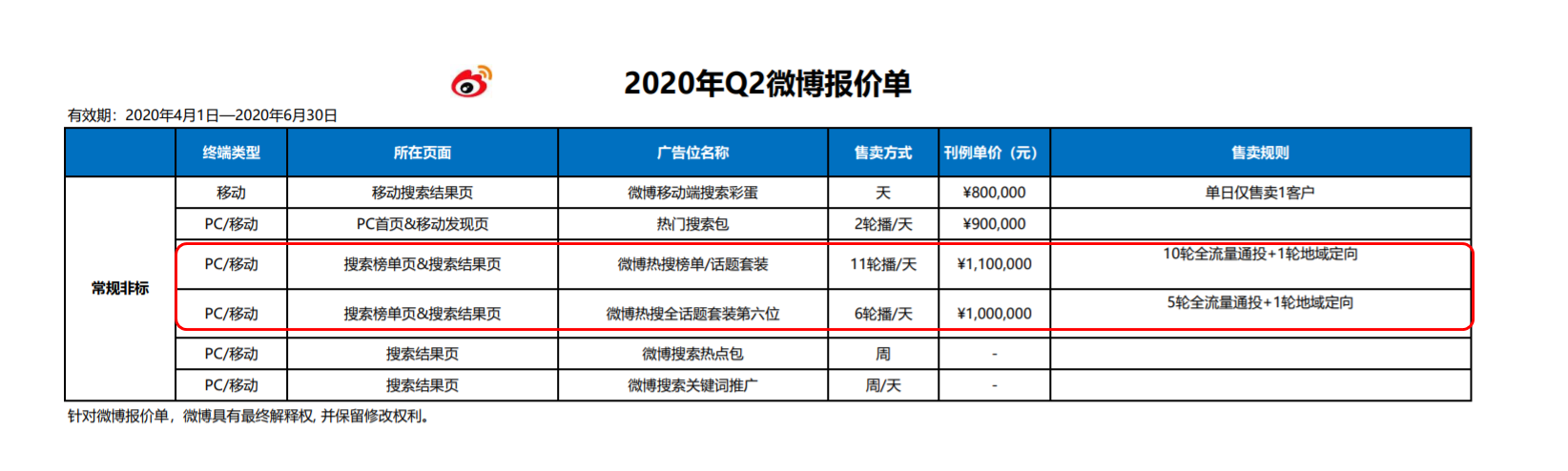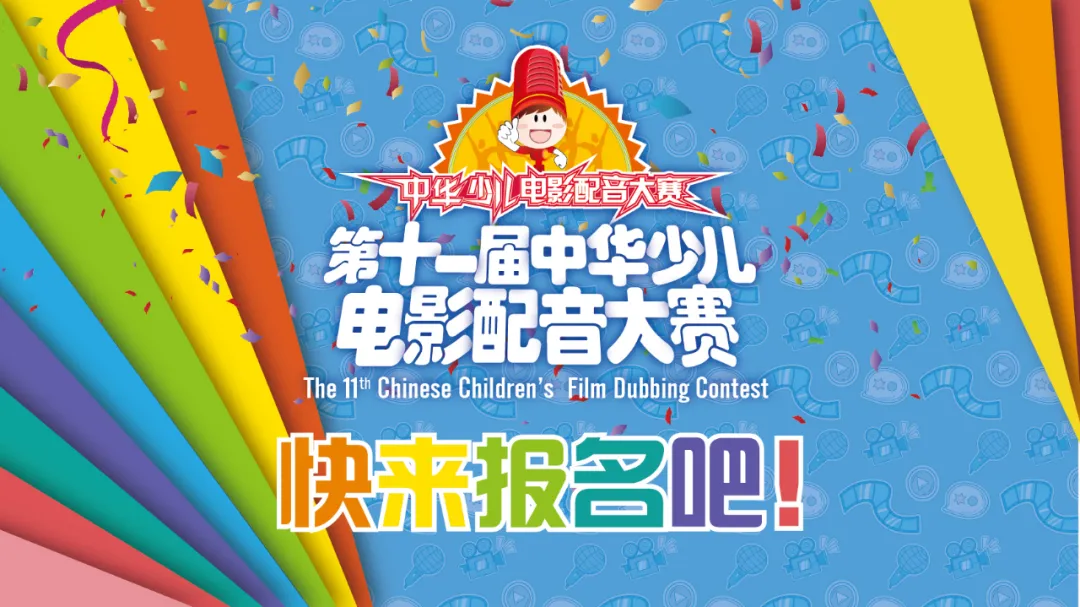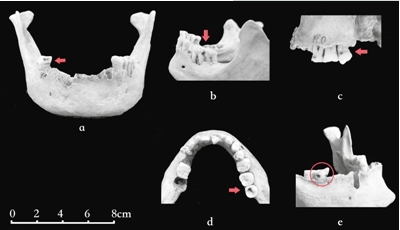《饥饿站台》是2019年11月在西班牙上映的一部高概念惊悚片,影片讲述了在一个垂直的监狱里,每天载有一定数量食物的站台从第1层降落到第333层,上层的囚犯肆意浪费食物,在食物上撒尿、吐口水,而下层的囚犯却只能饥饿到人吃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由加尔德·加兹特鲁·乌鲁蒂亚执导,伊万·马萨戈主演,是一部典型的高概念惊悚片。上映后影片获得了第44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午夜疯狂单元观众选择奖,豆瓣评分7.8分,近4万人为这部影片打出了5星好评。
上层人吃肉,下层人吃人
饥饿站台又叫监狱坑,总共有333层,每层有两个人,也就是说这整个监狱里共有666人,电影中的男主角格伦为了戒烟,主动要求进到一所建筑隔离6个月,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身处监狱,室友是因杀人而被关押起来的囚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每天他们的食物都是由98名上层囚犯吃剩下的残羹剩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无用挣扎过后,受不了饥饿的男主格伦也跟着室友吃起了剩饭,但万万没想到一个月过后,格伦和室友被安排到了第171层,这意味着每天站台上的食物会被上层人吃得一干二净,而他们彻底没了食物来源。
早有准备的室友在格伦尚未清醒时就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准备过一个星期后就把格伦杀了吃掉,幸好格伦中途得到了亚裔女人的帮助,完成反杀,而没了食物来源的格伦在今后的一个月里只能以吃室友的尸体苟活着,精神受到了大大的打击,渐渐沉沦在这座人吃人的监狱里。
《饥饿站台》作为一部典型的高概念电影,它利用残酷、血腥的视觉画面带给观众极大的冲击力,简单扼要的情节主轴与剧情铺设也让观众更容易地代入到电影人物中,电影以阶层为隐喻,在一个建筑中来谈论由阶层带来的格差社会,发人深省。
在这部反乌托邦影片中,那些看似不经意间的物体意象,却在故事里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将从电影里非常重要的核心意象、次要意象和衍生意象来分析影片关于阶层社会的思考,顺便谈谈这些意象对电影情节发展的重要性。
食物隐喻
核心意象——食物:用食物隐喻阶层分化,上等人不珍惜,下等人吃尸体
食物,是一切矛盾爆发的关键点。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意象,食物极大地推动了影片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朋友从老好人形象突然转变成一个吃人者形象,也都源于食物的短缺,就像室友对男主说的那句话:饥饿使人癫狂,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吃人要么被吃。
有意思的是,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短片《下一层》和大名鼎鼎的《雪国列车》这两部关于阶层分化的电影冲突点也表现在“食物”这一意象中。
短片《下一层》描述了一桌为食物而疯狂的饕餮者,他们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但面对盘子里动物血淋淋的尸体却宛如饕餮无度的恶鬼;而《雪国列车》更像是《饥饿站台》的横向版,同样因食物不足而爆发的动乱,同样用食物来隐喻阶层分化。
而《饥饿站台》中食物的意象则更为直白上层囚犯瞧不起下层囚犯,就是因为下层囚犯吃的食物是他们吃剩下的,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浪费食物,糟蹋食物,不管下层囚犯的死活,吃完后还要往餐桌上吐口口水,作为一部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寓言电影,《饥饿站台》里充满了各种隐喻细节。
人物隐喻
从人物设计上,这所监狱云集了各色人等,他们象征着不同立场的人。
“堂吉柯德式”人物——男主格伦
他如同堂吉柯德一般,奉行高尚的道德准则,坚信只要合理分配,人人都能存活。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的不切实际之人,他带着一本没有实际功用的书进来,一开始又不肯吃恶心的剩饭,还妄图以改革撼动管理者,拯救整个监狱。
实用主义者——老人狱友
在生活中,他是不如意的,深谙生存法则的老人,信奉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里,吃剩菜、割同伴、吃人肉,样样不在话下。或者,可以称得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要在努力攀上食物链的顶端。
理想主义者——面试官
她一心为公,不肯承认这里是监狱,而是“垂直自我管理中心”;就连来此地,也是出于帮助管理者实现“自发性团结”的目的,她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自己有限的两分钟时间内,践行着为大家平分食物的理念,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层人“留点吃的给下一层”,但是,没有用。
幻想主义者——找孩子的女人
十个月前她带着一把尤克里里来打此处,口中的儿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这个谜一般的女人本没有孩子,孩子是她幻想出来的,更或者,这个女人就不存在,是一个有行动目标的幻想者。
现实执行者——巴哈拉特
相对于其他人,巴哈拉特的特质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他的行动力超强,说干就干的性格倒是很讨喜,上来就扔绳子,顺绳爬上上一层;听到格伦提议分发食物,立马做其副手,付之实践。
饥饿站台路过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存挣扎,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在本质上都是被层级制度迫害的人,这部电影在试图告诉我们的,虽然反抗很难,反抗不一定成功,虽然上层人看不到底层人的苦难,反抗依然是必要的,只有试图打破被压迫的系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我是小新,想要获得更多娱乐新鲜事,请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