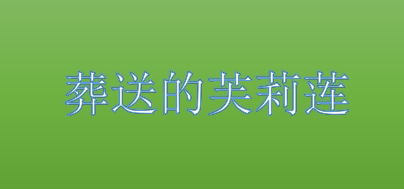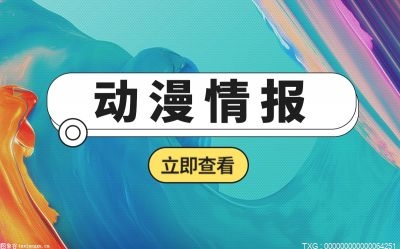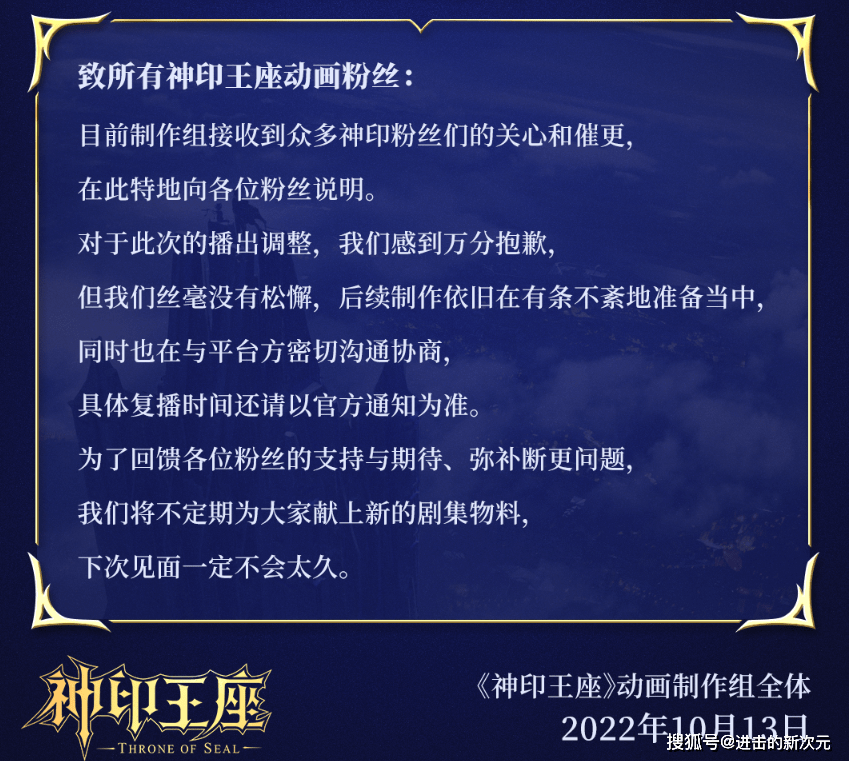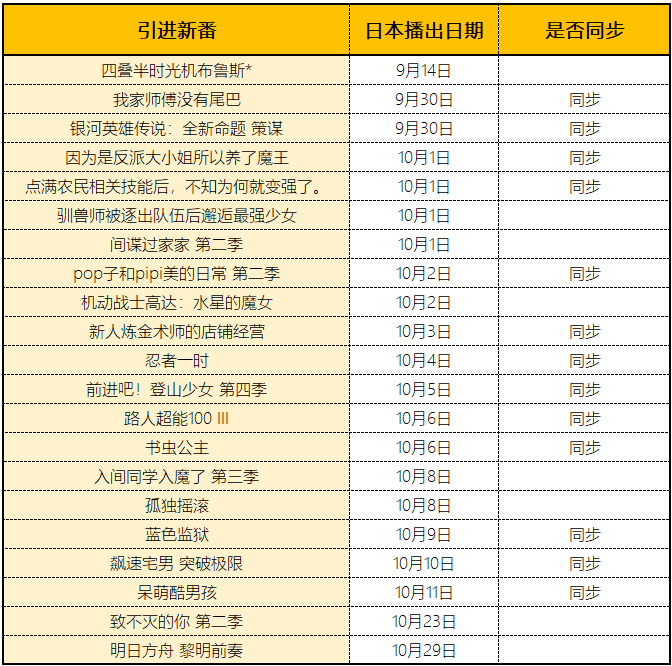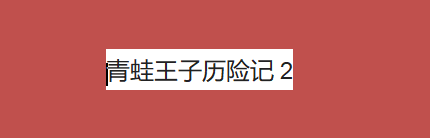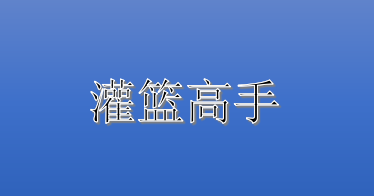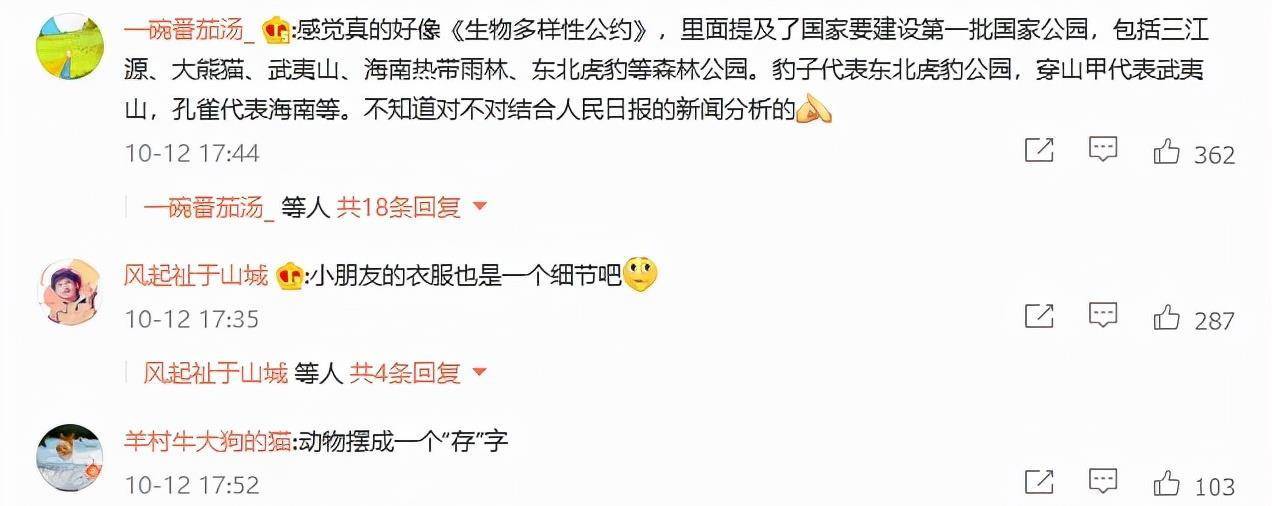作为“时空体”艺术,电影中时间的流逝必然要通过具象化的空间得以呈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也因此意味着,电影的时间与空间不仅是生活世界现实时空的参照,也是电影导演的主观意图与情感的表达。将电影界定为“第七艺术”的卡努杜也曾明确指出“电影艺术在于启发感情而非叙述事实”。
1903年,埃德温·鲍特的《火车大劫案》通过“场”与“场”相连接的方式建构起影片的叙事时间,这一按照时间线性逻辑重新编排空间架构的电影技法,标志着电影叙事时间、真实时间与放映时间三者的分离。
鲍特以“可叙述性”为原则,以直接切换的形式取代了默片时期“淡入”“淡出”的“时空转换”的形式,这意味着创作者主动干预叙事成为了可能。作为具有儒雅文人气质的导演,李安常利用空镜头和静物来完成影像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性过渡。
德勒兹认为,这种以“时空转换”为目的的过渡性空间,实际上是“它们自身蕴含或自成内容的载体”。
《色戒》中,王佳芝从香港回到上海,当中以“可叙述性”为原则所删除的三年,就是用空镜头来表现的。
空镜头将时间的绵延与情感的扩张重叠在一起,它不仅连接起《色戒》中的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同时,“时空转换”与人物命运的变化也通过空镜头被隐喻出来。镜头的转换不仅是叙事单元的变化,它还是直接的时间形式,是“情感转移”的手段。
为此,李安通常会选取与电影主题相契合的静物来作为过渡性的连接镜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上映时,李安曾表示,想借这一部电影与观众沟通一种“宿命感、一种生死与共的真实感和人生的虚幻感”。
显然地,李安想要借影片还原“所有人都在夸奖一个少年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天”的荒诞故事,进而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这种“欲说还休”的东方美学情思。
那么如何将这一种既含混又具有超脱意味的情感通过具象化的电影空间进行表达?
李安选择借助具有情感连续性的镜头的连接,借助从一个电影时空体到另一个电影时空体的绵延变换中,使观众获得对影像叙事及情感的潜在把握。这样,以静物作为过渡,镜头内的动作的因果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绵延的情感成为了观众最核心的时空体验。
接下来,我将具体来看李安电影中的空间角度有多高级?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当B班全体在秀场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安通过静物镜头的过渡,将叙事的时空转移到了“过去”的伊拉克战场。
在空间的构图上则与《断背山》相类似,作为静物的大树占据了画面空间的中心位置,通过微仰式的拍摄镜头,使天空的“空白”占据大部分的画面。
因此,在时空的绵延中,这一过渡性空间便又具有了一番中国古典美学中“留白”的余韵。“留白”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手法与美学理念,指通过以虚写实、虚实相生的手法达到“空”的精妙的艺术境界。
与西方美学讲究秩序、对称、均衡的“空白”不同,“留白”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指的“不是包举万象位置万物的轮廓,而是融入万物内部,参加万物之动的虚灵的‘道’”。
李安此处选取大树作为过渡性空间,尽管是“静止”的静物空间,但确实联合着记忆、感知与想象的“动态的停滞”,是需要观众以前一个场景的情绪与记忆的遗留来阅读当下影像的潜在运动。
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自然总是充满着无法从逻辑、理性上去解释的主观情感,具有生命属性的“气”与作为结构的“势”构成了空间和自然景观中的原始力量,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力量赋予自然景观更新与循环的勃勃生机。
在这一段落中,大树这一过渡性的影像空间既是前一个场景中比利强装镇定面对媒体的情绪遗留,也是对将要到来的十九岁少年的心境突破的隐喻。
随后,镜头不断拉近,比利在婆娑的树影下向施洛姆谈及自己对于战争的迷茫,对于杀戮的道德压力。
另一边,施洛姆则借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奎师那劝告阿朱那”的典故向比利“布道”:以超然的态度履行你的职责。这样的镜头运动事实上也体现着中国画的时空观念:让空间向远处铺展,时间在铺展中流淌。
在电影的尾声,结束秀场演出的比利拒绝了二姐安排的心理治疗并决定与B班战友一起重新奔赴战场。
在镜头的切换下,等候在秀场外的,不再是接送他们此次“荒诞”行程的豪华汽车,而是那辆战场冲锋的战车。当比利拉开车门,画面定格在战车中的摆件:象神。
在此,镜头虽未经过分切,但整体的节奏与情感在悄然间发生了转变。
定格的画面也将观众从之前紧张的姐弟对峙的情绪中抽离出来,进入到另一种相对平静、舒缓的气氛之中。
镜头所见的象神摆件,在印度文化中它代表着“去除障碍”的静物,成为了比利已逐渐治愈内在混乱与虚幻的抽象隐喻。
银幕中的静物画面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几近静止的绵延感:观众的目光随着镜头运动不断地延伸,从一个时空体到下一个时空体,从一个段落到下一个段落,然后进入时间与空间的汇流。
某种意义上,静物承载着“无限时间”的意义。德勒兹认为“变化的一切寓于时间之中,而时间本身不变,它或许只能在另一种时间,即无限的时间中变化”。
这一富有韵味的静物镜头,也因此具有了深邃的美学价值,它不仅是从情节中独立出来的直接时间影像,是一种运动连续体,也是通过眼前与过往、记忆与想象的连结所生成的独特意境,这是一种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独特的境界。
它与前一段落中战场施洛姆的树下“布道”形成了呼应,作为客观审美对象的“象神”,在此通过托物言情的形式,成为客观化的情绪的影像余留。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小胖胖趣聊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