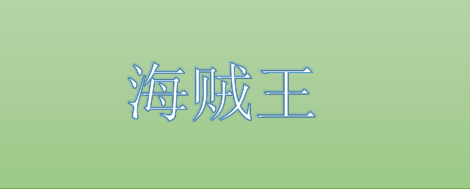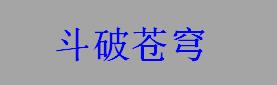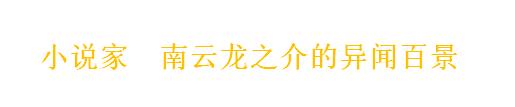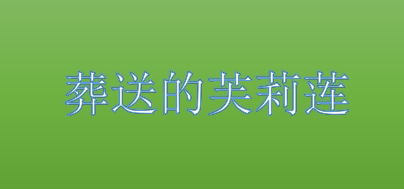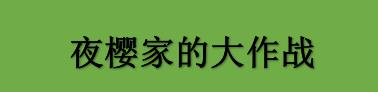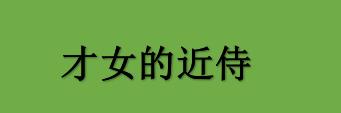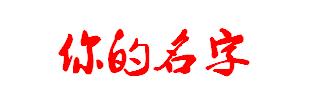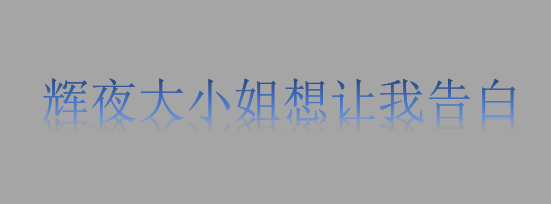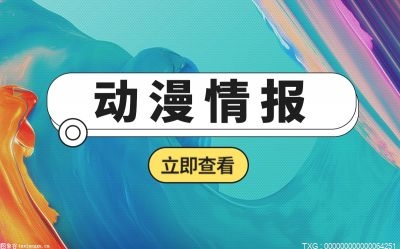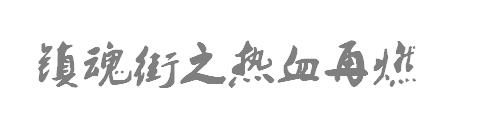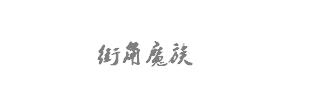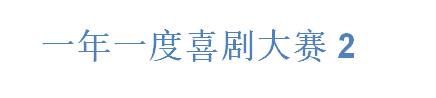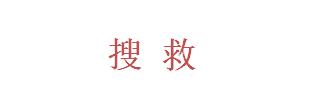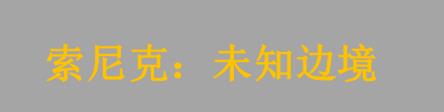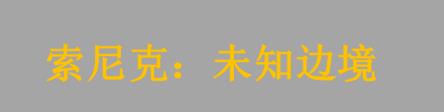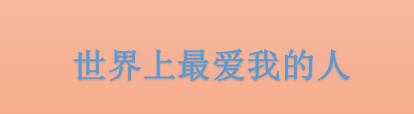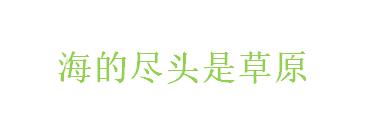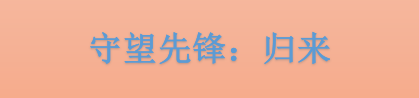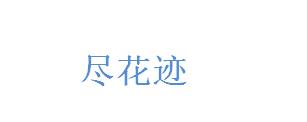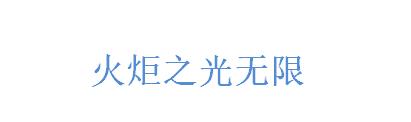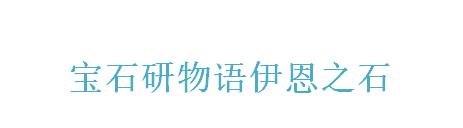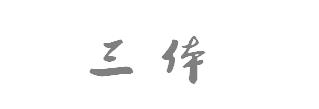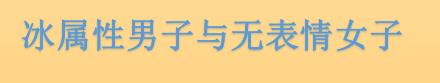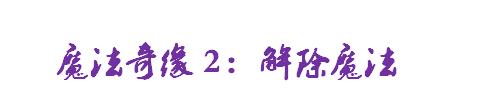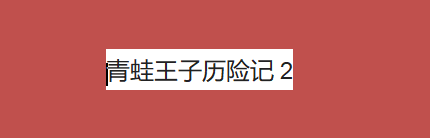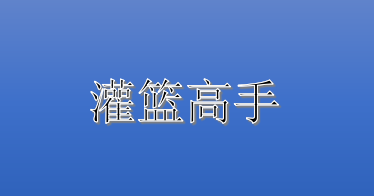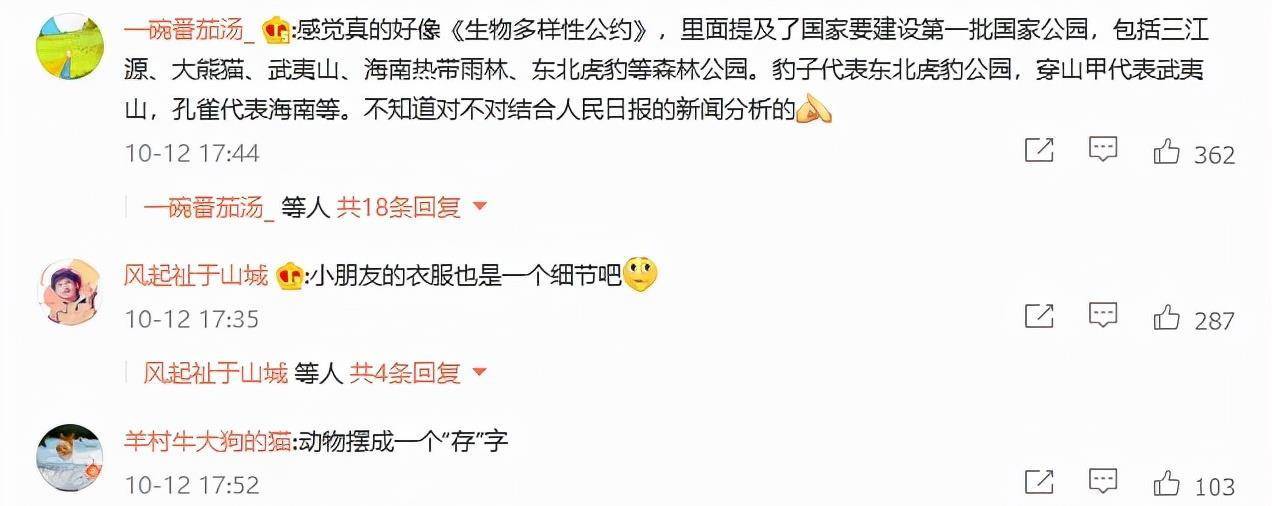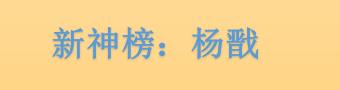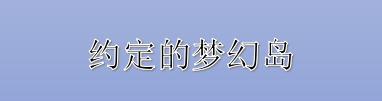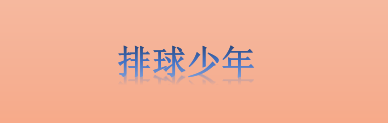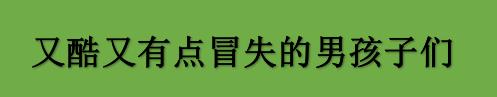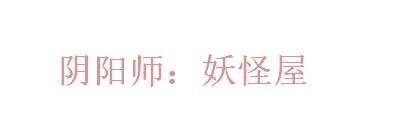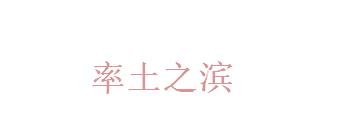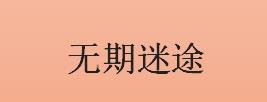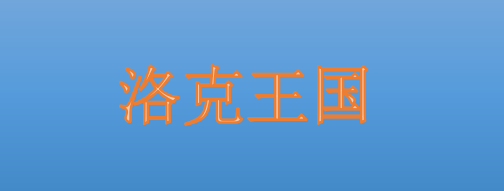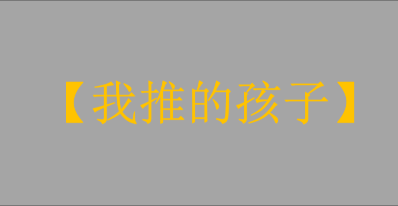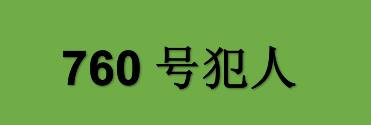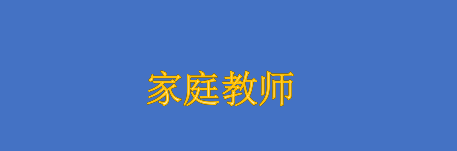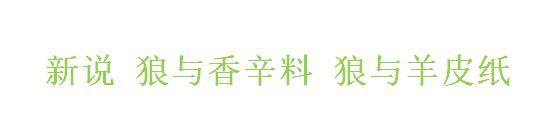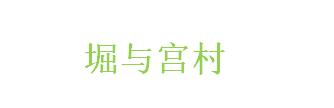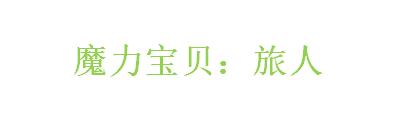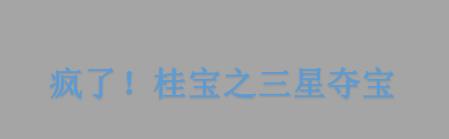文丨卿心君悦
我是在看完余华写的《活着》后,继而看的《许三观卖血记》,前者让我从福贵的一生中感受到了在命运的无常下生命所能蕴含的蓬勃、坚韧的力量;而后者则让我从许三观的一生中感受到了普通人之于生活的反抗以及我们自身在生活中奋战的身影。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这两本书都属于不难读且很容易、乐意读下去的作品,不需要用意识去强迫自己,仅凭剧情的推进,对人物的关注以及情感的代入就足以支撑我们将其读完。
同时,在阅读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都存在被剧情、人物触动心灵,情绪不受控制而落泪的情况,所不同的是在阅读《许三观卖血记》时,泪水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流。
触动我们的不仅有对悲苦的哀矜,还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使人在生活的困苦中负隅顽抗、不顾一切的缘由,大多都绝非是为了自己,因此在生活中前行的步伐,虽然艰难、凄苦、悲痛,但佝偻的姿态却总是会伴有渺小而伟大的光芒。
这就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在作品中许三观一共卖血十二次,失败一次,唯独最后失败的那一次卖血才算是真正为了自己——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这种结局令我们同情,但正因此也证实着他的伟大。
然而,许三观只是一个小人物,按作者余华的话来说:
“他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不多,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才不会迷路……”
可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他却拥有着为了家庭、亲人牺牲自己、甘于奉献的品质,而这个品质其实也被无数人悄悄地拥有着,看着他的生活,如同看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陷入其中,感动其中:
他没有梦想,却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让家人生活的与身边人一样;
他没有本事,却可以通过牺牲自己,以卖血的方式让家庭度过难关。
或许,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值得许三观开心、欢笑的事情,但故事中的许三观又似乎生活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或许,这就是余华在《活着》中所说的那句话,“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旁观的我们所看到的未必是当事人的感受,自己生活的如何,最终还需要自己去鉴定,而非他人的评价。
除了当事人,谁也没有资格,也没有那个能力通过一件事、某一时刻去评价那个人究竟生活的是否幸福。所以,当我们在作品的结尾处,看到许三观因没有卖出血,失神、悲痛着在街头一圈一圈无意识地游走时,我们不该因此去判定许三观的一生是可怜的,不幸的。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事件中的情绪会占据许三观整个生活中喜与悲比例的多少,更无法因为这一件事为作品的结局定义成悲剧,相反,在最后许三观的三个儿子都健康地在身边且各自成家,许玉兰完成了许三观那吃炒猪肝,喝黄酒的愿望,我倒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喜剧的结尾。
就像我们一样,拼尽全力地在生活中反抗,不就是为了家人的平安幸福,既然家人安在,我们又何来悲伤,又何该因一时的悲伤否定、悲化自己的一生。
不是亲生的一乐,是对亲情最残忍的反思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除了对卖血的缘由、经过描述外,作者着墨最多的就是关于许三观与一乐之间情感的转变。
许三观与妻子许玉兰生有三个儿子——一乐、二乐和三乐,其中许三观最喜欢的是一乐,可偏偏天不作巧,一乐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事实成为了许三观持续半生的痛:
“我做了九年的乌龟,我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
然而在许三观十二次的卖血中,绝大部分又是为了一乐:
一乐打伤了方铁匠的儿子,许三观第三次卖血就是为了给一乐支付方铁匠儿子的医药费;
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乐突患肝炎需要到上海治病,许三观一路五次卖血积攒药费前往上海。
不是亲生的一乐,却是许三观花费心血最多的儿子,而不是许三观亲生的一乐,却又只认许三观这一个父亲。我不认为这段剧情是对许玉兰过失(也不该算是她的过失)的指责,也不认为这是旨在对某种伦理关系的批判,我反倒觉得这是余华借用极端的剧情,将亲情、血缘与感情三者完全剥离分解出来,意在让我们从中反思亲情之中那份感情的由来。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亲情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好比人出生后天生的印记,这种印记促成了一群人之间天生就拥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默认这种联系为超出寻常的情感,因为这种印记的特性,他们又会对这种情感带有特殊的期许。
由此促使着大多数人在亲情中处于获取为多,奉献为少的状态,过程中他们不会为付出情感的多与少而心生惶恐、顾虑,这种“理所应当”、“肆无忌惮”的态度正源于构建情感的印记牢不可破又无法消除。
但也正因如此,当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与生活的压力等等外界因素致使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致使一些人对于亲情的认同感越来越低,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觉得亲情不如其他的感情更为浓郁。于是,一些人开始质疑亲情,甚至以世俗的偏见予以诬蔑。
而《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与一乐之间的情感转变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并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许三观得知一乐不是自己亲生的后,对其百般疏远。而一乐呢,虽然知道自己与许三观没有血缘关系,也曾因许三观冷漠的态度,离家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可到头来在一乐心中默认他的父亲就是许三观。
一乐对许三观的依赖与情感认可,不源于血脉但胜似亲情,因为许三观对一乐的关心、爱护与养育之恩。而许三观最后从心里彻底接受一乐,也是被一乐对他的依恋、感情所打动,由此那阻碍亲情的隔阂豁然一空:
“好儿子啊,一乐,你真是我的好儿子,我养了你十三年,没有白养你,有你今天这些话,我再养你十三年也高兴……”
亲情之间也有亲疏之分,为何,这就取决于血缘以外的感情,是那种不是亲情的感情决定着亲情的浓与淡。《增广贤文》说:“是亲不是亲,非亲却是亲”,说的何尝不是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感情才是为一段情感定性的关键。
我想对于亲情确实应该转变一些观念了,凭借血缘、责任等因素去维系亲情或许才是让其一触就破的最大元凶,缺少了感情的交流与孕育,单独的亲情又能向哪里获取养分呢?这或许也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达萨最初惊讶竟察觉不到任何与亲生儿子之间感情的原因吧。
普通人的安全感,往往源于自身拥有有价值的牺牲物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最催人泪下的一幕莫过于许三观最后一次卖血失败后在街头的痛哭,过程中许三观喃喃自语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他的心酸,也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实中的烦恼:
“以后家里要是再遇上灾祸,我怎么办啊?”
在许三观以往的生活经验里,即便生活真的遇到难以跨越的坎,他也不必太过担忧,因为他心中有底,知道真到危难的关头,都可以通过卖血的方式来帮助家里解决困境,比如一乐打伤方铁匠儿子那一次,家里多年积累的家当被无情搬走以抵销药费,许三观就是通过卖血的方式让家里回到了原本的轨道;比如在那个特殊时期,当家里人连续喝了五十七天玉米糊后,许三观又通过卖血为全家人缓解了那时的苦;比如家里无钱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队长时,许三观以卖血缓解了当时的急迫;更比如当一乐重病需要到上海治疗时,若无许三观一路卖血很可能一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丧命……
在漫长的岁月中,许三观早已经把卖血这一途径作为抵抗与反抗生活的最有力的凭借,这也是许三观面对生活苦难与考验的底气所在,哪怕这种方式会消耗力气、热量与生命……
看完《许三观卖血记》后,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思考在我们普通人心中安全感的构成,在以往的认知中,安全感应该来源于我们所拥有反抗生活的武器,或者说是底牌,即便这个存在不是绝对万能的,但只要可以解决大多数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拥有“它”,我们就拥有了安全感。
但从这部作品中,我又发现了另一种安全感的由来,和我曾经的认知类似,但又存在某种细节上的差别,存在于自身以外的东西不算是安全感,那种由心的踏实主要来源于完全属于我们自身,而且使用起来要有一定损耗,还要附有一定限制条件的东西,才可能是我们内心所接受的安全感。比如,在作品中许三观不会把力气与健康作为安全感的来源,而是把身体中的能卖出去的血作为安全感的来源;比如,现实生活中我们有钱未必会有安全感,可是有房产却会觉得有安全感,因为房产是自己真正拥有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换钱……
由此概括来说,安全感这种东西,虽是我们自身的感觉,但需要得到我们自身所认可的,同时能够明确是我们自身拥有的、有限的,使用过后会有消耗的某种事物或东西。
这种对安全感的认知对吗?或许也不该用错与对去衡量、判定,因为在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心中这就是安全感的由来。只是若是这样去寻获安全感,又会导致我们在生活中错过很多乐趣,徒生无畏的烦恼,就像许三观因为卖血失败而悲痛不已一样,实际上呢,正如许玉兰说的:
“许三观,我们现在不用卖血了,现在家里不缺钱,以后家里也不会缺钱的。”
其实,很可能一家人身体健康就已经拥有着安全感,我们有一技之长就拥有着安全感,国家富强、经济繁荣就拥有着安全感,但若非要在这种状态下过度的“居安思危”,很可能即便拥有着安全感仍会苛责自己去寻获某种意义上的安全感。
这不就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吗?
毕竟我们总是担心可能的危机,又哪有精力去关注当前的美好。
卿心君悦,一个情感观察者,Ta说书评人、影评人。用文字温暖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