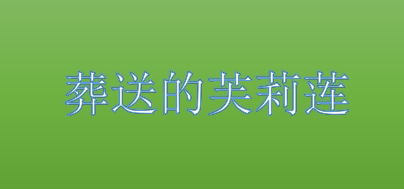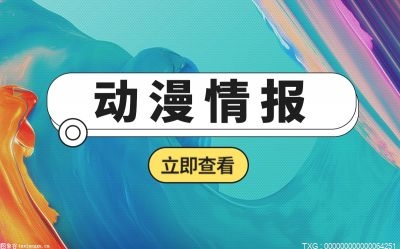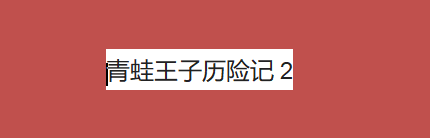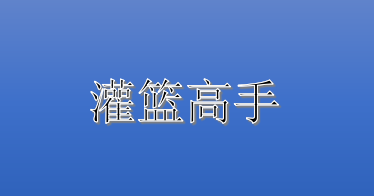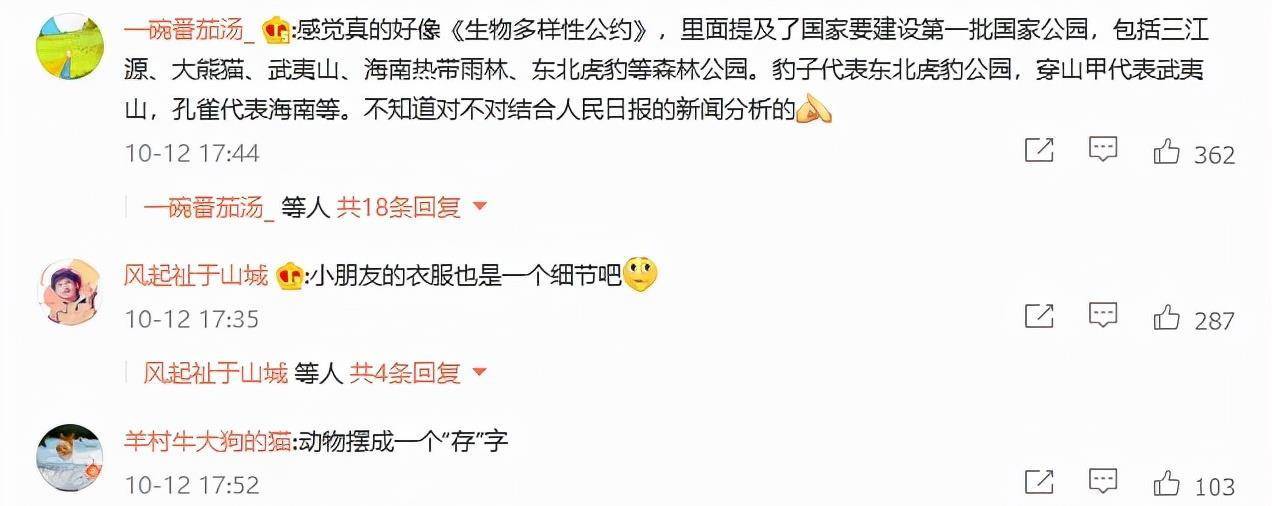首尔市长去世后,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高墙内的我们,哀悼之外也多了一份无奈。
我们似乎很难去改变什么,或者说我们压根就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有网友调侃道:
丰富的社会活动与离奇的历史大事件给韩国电影人留下了丰富的素材。市长失联注定会有《南山的部长》一般载入韩国电影的史册,但在传统封闭式的建制下什么也无法改变。
玩笑归玩笑,但韩国电影的确讨喜。在今天好莱坞全球化的扩张与渗透下,中国的观众们开始对好莱坞类型电影出现了审美疲劳,于是转头便拥抱了韩国电影。
看到电影
毋庸置疑,韩国电影具有传奇性。
即便是它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德国表现主义,中国寻根文化的电影理念革新的运动,但它却凭借着类型电影的本土化成为了新一届亚洲电影的代表与领军人物。
它有“搞艺术”的朴赞郁,“搞哲学”的李沧东,搞“艺术与商业”融合的奉俊昊,还有时不时给观众们带来惊喜的张宰贤,张宰贤,李濬益,黄东赫...
他们都凭借着独特的作者风波,以艺术或类型电影为阵地,勾勒出了韩国的“百城众生相”。
在自省与逃离的同时又满足了全球观众们的“猎奇”的心理。
《哭声》:借以封闭与半封闭的压抑空间内,灰暗影调所笼罩的交叉式宗教符号被模糊,人们的信仰从“坚定”到崩塌。
《寄生虫》:借以三个家庭的故事,直接还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便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财富权力的阶级性跨越,但是上层与底层之间的鸿沟却会永远存在。
《燃烧》:借以“大饥饿与小饥饿”的故事,看到韩国“出租房主义”的现实困境之下,年轻人的焦虑与无奈,以及思索“场外”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即便大众不是韩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但也借以韩国电影看到了隐藏在合理性背后的问题。
或是近邻等综合缘故,不少的中国观众们也或多或少的有着强烈的代入感,他们把韩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也下意识的认为是我们的问题。
面对韩国电影的强势的文化输出,有电影人则调侃道:“韩国人,拍了中国人想拍但不能拍的。”果真如此吗?不是。中国电影并不缺乏“辉煌时刻”。
我们既有《黄土地》《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我不是药神》《天长地久》,中国电影从来就不缺乏艺术性与现实感知,思想贫弱与固步自封才是当代电影存在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过去,世界电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电影,亚洲电影需要满足的是西方想象中的亚洲来获得“世界”的认可,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与时代的更替,现在的西方电影需要的是借用亚洲电影来审视自我。
中国电影的思想贫弱与固步自封,以一种“正确性的霸权”形式阻碍并伤害了中国电影的“包容性”,这使得中国电影落后在这场全球性的文化竞赛。
而韩国电影到底做了什么使得它们能够迅速的走向全球化的通道,并以一种平等对话,交融的姿态去构造自己特有的叙事策略,走向了与好莱坞对应全球化路径的截然相反的道路。我们中国电影又能从韩国学到什么?
世界性文本
我们常说,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模式正在陷入一种“俗套”与“僵化”的模式,摆脱不了的“中心与个人英雄主义,三幕式,女权主义,白人救赎主,神奇的黑人”的创作困境。
但就从漫威系列,DC系列,以及星球大战系列,以及类似于《头号玩家》大片的全球票房结果论看,好莱坞类型电影依旧占据着全球电影市场的大半壁以上的票房统治号召力。
它的全球化的策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旧盛行与被接受,其原因除了庞大与领先的电影工业支撑外,还有着叙事模式开放性的包容性。
这个开放的叙事模式使得它可以融合且多变性的添加文化元素,但却能够适应任何时空带来的挑战,保持“个人主义”的优先地位。
比如,在《变形金刚》的系列中,它就巧妙的融合了香港所代表的符号元素,这极大的满足了中国观众们的猎奇的心理。而《速度与激情》的系列中,除了让男性热血沸腾的极速飙车外,还带着观众们把世界的景观都“逛”了一遍,即便没有出门却也看到了世界的浩瀚与壮观。
这样的叙事模式带来了电影的“互文性”。狭隘来说,这个“互文性”就是,电影输出文化与内容的同时,观众们也同样把思考与内容反馈给电影,这里也就是说,互文的存在给差异构造了一个“中间性”的空白地带,在这个地带里面任何物质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对话。
韩国电影自然也是依靠着这个“中间性”的空白地带引发全球观众们的共鸣,只不过它与好莱坞的选择的的“填补元素”不同。好莱坞是用意类似于“空间场景”,“相同道具”,“异国风情”等外化的元素去构造“奇观”的内容,而韩国电影选择的是“人本性”的元素,即有关于“生命,财富,权力,性,哲学”等人类追溯的永恒问题。
韩国电影始终根植的是对本土文化的寻根探索,但他们在探索的时候却采用的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他们"形而上,也不形而下”,在一个空白的空间内构造了多元化的世界,这使得他们脱离了地域性的作者身份,从而有了以电影通道,超越文化与地域性隔阂的文化碰撞与输出。
地域坚守
地域性的生产,类似于一道万里城墙,它抵御了外来事物的侵入与骚扰,守护了一方水土,但也形成了明显式的“疆域”划分和固定式的流动性,里面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也急不来。阻碍了文明间的碰撞与融合。
地区性的电影想要走向全球化,就必须要打破自身的地域限制,创作者要超越其自身的民族或者地区的固定式思维。这就要求导演在追求作者意识的同时,一定要平衡它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电影主题需要上升到更高更广的格局中,合适的表达电影空间就显得格外重要。
大部分的亚洲电影在处理地域化设计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无地域空间”也就是说通过改造地景的方式,把它归纳成故土或者区域性的土地。例如:
黄渤的《一出好戏》的环境背景是在日本的屋久岛,取景,然后再回到上海取景。
王家卫的《春光乍泄》是在阿根廷取景,然后再回到香港。
蔡明亮的《脸》虽然是再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取景,但是拍摄的只是地下室的那个场景。
从功能性角度来看,无地域空间的取景说明了全球化的同质性,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而从空间的情感来看,无地域空间显然在隐喻着自然与人的离散。
韩国电影则不是,在全球化浪潮与亚洲电影“无地域空间”的运动中,韩国电影坚守了自我。它有着明确性的地域化标志,随处可见的是,象征着希望或者是困境的地域性的符号建筑与标志。
一如李沧东《燃烧》里面的出租屋,奉俊昊的别墅与半地下室的对立。这些极具地域性象征的隐喻在转化成了“跨地域性”的符号。这种“跨地域性”的符号依旧是有标志性建筑所承载,但内容却变成了超越性的视点与幻影。
文化距离
韩国电影的对话文本,大多通俗易懂。观众如果能看得更深那自然是件好事,但即使看到更深度的东西,表层的故事也总是能让观众一笑。
韩国电影的文本在创作的时候始终是一种立足于本土的内容,但视野却遍及道了全球的地域空间,它缩小了不同观众之间的文化差异,让韩国的本土故事与世界产生了共鸣,并随后推动类型文化的输出。
当然类型文化始终是韩国电影的基础,他们的大部分电影是类型电影,而类型电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满足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因此从这个点上来说,韩国电影在创作的时候便是直接迎面走向人们的内心深处的痛或者兴奋。
“在过去,比较的基础始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起点也来自欧洲,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的谬论,不可能所有的大事件都发生在欧洲,然后再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因此当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具有单一性源头说法的时候,韩国电影自身文化基因的内容就被视为论据无限制放大。
它所呈现的现实困境,也成为了超越性的文本指向了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现实的缩影,而造成这个“缩影”的形成正是今天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结果。
韩国电影做的就是找到一种文化上“距离”,这种距离使得韩国电影有了不同寻常的视点以及错误的观点,那些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也就成为了跨越文化地域高墙的隐喻。
距离间的美,反而让韩国电影不再受到现代性空间的限制,交流间的障碍,实现了东方式的电影奇观的交往模式。
当我们回顾韩国电影,他们没有经历电影的运动改革,却从借鉴和模仿之中不断探索出韩国本土类型电影的铺垫文化之路。
他们善于自省,敢于批评,勇于建立,坚守自我,而这些恰恰也正是中国电影人需要学习与进步的东西。